19世纪中叶,西方“科学”概念传入中国,现代科学学术体系开始在中国落地生根。生理学、物理学、生物学等西方科学学科成为时人“开眼看世界”并融入世界现代化潮流的路径,大批有志青年纷纷留学欧美或日本,在接受西方科学学术训练后将其带回中国,并联合同志组建学科社团,推动相关学科的建制化发展。近年来学界对中国近代历史上的科学人物、科学社团与科学学科等问题,进行了较为细致的梳理与研究,基本理清科学学科传入中国并“落地”的经过,主要科学人物的思想贡献,以及学科社团在促进科学知识交流与传播中的重要作用等。但作为一个整体性概念的“科学”,却在众多研究者各自关注的议题中被分散拆解,使得诸如不同科学学科、人物、社团研究间的比较性对话被忽略。
2024年4月19日,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主办的“学科、社团与人物:近代以来科学社团与学科创建的若干问题”研讨会在逸夫楼校董厅召开。中国科学院院士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名誉主席韩启德教授莅临会议,并就如何理解展开医学史研究,以及书写历史上的科学家等学术问题作了大会发言。会议召集人,复旦大学历史学系高晞教授表示,此次会议为进一步推动有关近代中国科学学科、科学人物与科学社团的历史研究,增进关注不同科学学科研究学者间的交流对话,以期较为全面地理解近代西方科学和医学知识体系在中国演进的本相。本次研讨会关注近代中国诸学科的接受、草创及其地方性社团展开,殊途同归,近代科学学科正是通过不同渠道、按不同方式,以知识代理、科学社团与人际网络为推展,构成中国近代以来的旧学科与新学科的转接节点,由此,两个维度的交叠就构成了本次看似“松散”讨论的题眼所在。

中国科学院院士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名誉主席韩启德教授作开幕发言
韩启德院士的开场致辞指出的,医学史、科学史的底色是史学,关于这个问题,学界可能有不同的说法,甚至有所争论,但是我认为史学的背景与方法是必不可少的,关键是医学与历史交叉的具体研究方式,需要认真地思考,相较于历史学家去学习医学知识,并能做到上手实验、治疗并做手术操作,由培养已掌握医学知识的专业人才去做医学史,给他们进行史学训练,学会以并掌握史学认识与方法或许更具可行性。韩启德院士对与会的青年学者和学生说,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如果沉下心来,去做医学史还是能有一番天地的。因为相较物理学需要具体的运算公式来支撑,医学本身就带有更多的人文性质,无论是在研究领域,还是操作层面都更适合从思想、社会的视角来切入,展开思考与研究。历史研究除了梳理史料,还是需要有理论框架,对收集整理的史料要有分析,研究问题应该有所上提升,研究历史问题、分析史料,最终还是要思考历史意义,这才是历史学、医学史和科学史研究的价值。

《学科、社团与人物:近代以来科学社团与学科创建的若干问题研讨会》会议现场照片
本次研讨会共召集10余位经过良好史学训练的青年人,以及有着医学和科学知识背景的博士生,他们或是积累多年、或是初涉探索该话题中青年学者,尤其是三位在校的博士学生的探索性报告,显现学界新鲜血液意在向欲济无楫、徒羡有鱼者传递渔经猎史的脉搏,稍显拍得鱼惊不应人。
上午场的另外两篇发表则因选取案例的不同特点,更多是呈现了材料挖掘的魅力。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的姚霏教授的《从“癌”到“肿瘤”: 新中国肿瘤学科的创建》由上海城市史方向出发,关注上海对新中国建立系统的肿瘤学科所起到的影响。一方面北京协和医学院培养了诸多肿瘤学科人才,像毕业生张去病成为上海肿瘤放射科的创建者,另一方面像上海设有利用庚款建立的中比镭锭医院,其中顾绥岳为后续上海提供了病理科的方向,之后又与留美归来的李月云医生开设的中山医院肿瘤外科合并,成立上海第一医学院肿瘤医院,为后续的学科发展奠定了组织机构基础。苏州大学心理学系的范庭卫副教授的《丁瓒与二十世纪中国心理卫生工作》则钩沉了中国近代心理学家丁瓒的人生轨迹,其先后在南京、北京与芝加哥学习,兼及具体个人的心理分析与社会统计的(学校)心理卫生工作;在50年代期间又积极学习与倡导巴甫洛夫学说的机体整体性和神经论思想,如此建设医学心理学与指导神经衰弱治疗等工作为心理学在当时时代背景下的保存提供了一定帮助。
正如韩启德院士所指出的,科学史和医学史研究要注重史学面相,本次研讨会便是侧重由历史学维度对科学史、医学史的观照,以期在搜罗、整理材料以反思既有单线叙事的基础上,尝试由个案切入有所理论创见,像上午场两位博士生的报告便体现了这般旨趣。
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的博士生梁佳媛选取燕京大学生物学系美籍教员博爱理(Alice Middleton Boring)为代表人物,报告了《知识的地方性——以燕大生物学教员的研究转向为例》不过,梁佳媛的研究并非将其叙述为西学东渐“移植”话语下的复写个案,而是剖析博爱理在1930年代由实验性转入描述性生物学的背后动因,这一看似逆学术潮流的转型实则蕴含着具体的学术与文化因素:一方面实验胚胎学在20世纪初尚未觅得机制性的合理解释,仍裹足于传统的预成论与后成论争议,故博爱理的几位导师先后转向能与新兴实验手段紧密结合的其他方向,她本人也就相应较难接触该领域的系统训练;另一方面博爱理在华期间受实验室条件的限制与中国博物学的理念投射,也倾向基于中国丰富的生物资源展开分类认知的系统生物学探索。博爱理的案例提供了对称性审视在华生物学研究的契机,一者在于地方性的分类对象调动起既有生物学框架的重估工作,一者在于研究方法与学科也是基于地方性经验的归纳、转化与建制:在某种意义上,姜丽婧(JHU)所勾勒的社会主义时期胚胎学(socialist embryology)调动起另线思想资源的地方性尝试亦可视为其后续回响(Jiang, 2017)。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的博士生林梦月则是聚焦于中国实验胚胎学与细胞学重要开拓者朱洗,她在《互助:生物学家朱洗的进化思想及社会主张》一文中留意到他科学研究外的科普与社会思想面向,特别是其《生物的进化》一书在30年代开始写作、50年代最终出版两个时间节点收到似显对立的评价。朱洗留法期间受新拉马克学者德拉日(Yves Delage)观点及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影响,在学理与思想倾向上趋于反思达尔文更多在生物层面、又被接受者主观拓展为社会铁律的自然选择说,相信“互助”是生物界在竞争现象外的另一要素,早期《生物的进化》手稿便是朱洗此般认识的投射;而在50年代虽已删去敏感部分,但因达尔文学说被视为启发马克思的自然科学三大发现之一,朱洗的互助论说在此语境下遭致非议。朱洗在生物学领域经法国转接而来的学理路径,提供了近代中国反思天演单线竞争观念的具体案例,并非如某些学者以中西新旧、科学革命这般宏观层面之正反合来简单解析“公言”(Peng, 2018),实有学说本身演进、具体接受时间差等历史细节与思想契机;并且这般思想史意味的研究同样可与自然科学研究互为启发,当下生物学界亦逐渐反思达尔文学说奠基而来的现代综合(Modern Synthesis)框架,朱洗接受时已显错置的新拉马克主义又成为拓展演化综论(Extended Evolutionary Synthesis, EES)的思想资源,像有机体同样能借由影响生态系统及其物质能量流来非基因地继承自然选择压与构建生态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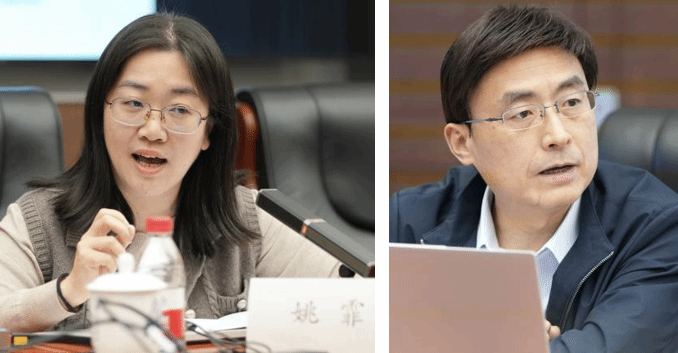

发言者:左上:姚霏 右上:范庭卫
左下:梁佳媛 右下:林梦月
而复旦大学历史学系的刘小朦的《矛盾的药学革命:国产药物、外来技术与民国时期上海的制药革新》则指向了在科学与思想维度的医学革命之外、侧重技术与实践的国药革命。这一运动相较而言更多是以企业家与商人为主导,刘小朦在其中特别选取粹华与佛慈两家药厂来呈现。前者创建人李平书有感于上海1919年的疫病应对,认为中药萃取制成丸剂、片剂等形式相较汤剂更具便利性以应对紧急情况,其商品粹华药水便是提取中药有效成分制剂的尝试;而后者则由太虚大师的俗家弟子玉慧观设立,一方面自称是粹华药厂的继承者,并创办《科学国药》期刊等在传媒层面宣传,另一方面在产品层面也经历了着重无量寿电化参胶、国药提精与改良国药三阶段,各阶段也因不同信念呈现身体观念、西方技术与国药成方上的各异辩护或证言。该研究是刘老师既往明清药材市场论题的自然延伸,亦呼应了时下科学史学界侧重技艺维度的转向。相较刘小朦的研究,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的崔军锋副教授则归纳了近代以来,学界三类态度在脉学领域的投射,诸如四诊合参、中西合参以及改造为中医诊断学等尝试。
江西中医药大学中医学院的程佩副教授在《医易学在当今中医学中的定位》一文中所探讨之医易学的定位困境,依托大数据来归纳出生时空与体质状况间的关系,则是重审自然之不均称性的有益尝试,由海量实践案例的统计来重新定位既有的模型;不过,有失偏颇的一点在于,报告为凸显医易学定位的升降沉浮,研究叙事似采用了晚近科学化以来逐步消亡的悲剧化与单线叙事,但至少像其中所罗列的章太炎就并非只有单面。
相较以上注重学科知识/实践和代表人物,余下四篇发表可相应归入科学社团与人物群像的关注范畴。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赵婧副研究员的《知识与性别:近代女性医者社群研究》报告梳理了近代中国女性医者社群研究的学术史,一方面相比讲述精英医生,具体的女医社群已然成为社会史研究的热点,但也需进一步关注作为男/女医对举之外女医群体内部的亚社群,另一方面也不可忽视女医群体在既有社会网络中的医疗倾向与能动性,像女医开业所借助的社会网络、利用男女有别的性别规范来建构女医相关专科的专业权威皆是例证;也正因聚焦于具体历史细节,报告最后也指向了比较的视野、对象的拓展、资料的挖掘等未来研究的可能性。
浙江大学历史学院的姬凌辉研究员便是多方汇集档案钩沉了战时中央防疫处及其生物制品事业的发展,他的《抗战前后中央、西北防疫处及其生物制品事业的发展(1933—1949)》报告,通过陈宗贤、汤飞凡两位组织领导人与组织迁转大体划定该机构的两个时代,试图勾勒这一行政、商业与科研交集的机构进行运输、检验、流调报告分享的运作细节;方益昉则提醒在该机构与国际联盟的资金、数据与知识的全球联结外,当留意同时期红十字会这样民间群体搭建疫苗流通网络的活动。
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人文学院的庞境怡讲师的报告分析了传统医会/社如何过渡至近代医学会的历程,她在《晚清医学团体的重现与兴起(1860-1912)》一文中谈到这样的医学团体实则在变法改革时期担荷了医事制度与中西医学知识传播等多重功能;值得注意的是,相较医学专业群体内部组织的医学会,官绅筹设的医学会似未能长期延续,这背后是否存在“会”这一组织理解嬗变的因素,或是清末央地关系下放与回收的影响。而像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的博士生戴淑琳的研究兴趣则从当代中外科学文化史的角度,考察并评估社团在学术交流中所起的作用及政治环境对学术文化流的影响,她的报告《用医学架起中日两国的桥梁:“日中医学协会”的创立与发展(1972—2023)》辑录了延续至当下的日中医学协会之发展历程,该学会在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背景下逐步建立,提供了中日间医学互访、进修交流与技术支持等多种协作的途径;不过如此组织材料有陷入协会网站自我形塑叙事的风险,与会学者也建议由口述史和具体档案材料来寻找单线叙事外的更多可能面向。


左上:刘小朦 中:姬凌辉 右上:赵婧
左下:崔军锋 中:程佩 右下:庞境怡 戴淑琳
本次研讨会取学科知识/实践与人际网络互为抓手,数篇报告呈现了当代青年学者努力将历史的疑问转化为可以解答的史学问题的研究旨趣,这样的尝试与努力正在显现力量与影响力,相较伟大医生传记与学科创设筚路蓝缕的叙事,这自然由史学视角补充了置于具体情境之下的切入视角与历史细节(内→外);与之相对称地,学理的内生脉络同样不容忽视(可参以上两位博士生报告中的地方性展开),即便不以思想本身作为研究话题,至少也有必要将学理与人/物的(全球)脉络作为对等考量的要素,此般筋骨万不可简单封装透入阶级、种族与性别的三棱镜便告万事大吉(外→内):科学/医学之内外史的权宜划定当成为此般递归的纵云梯,而非徒增畛域之别的厚障壁。韩院士在开幕发言时指出,本次研讨会,我想是一个非常有益的尝试,一方面是有确定的主题,另一方面是小范围的公开讨论,这也是我抽身来参与这次会议的出发点,我非常期待本次研讨会能取得积极合作的圆满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