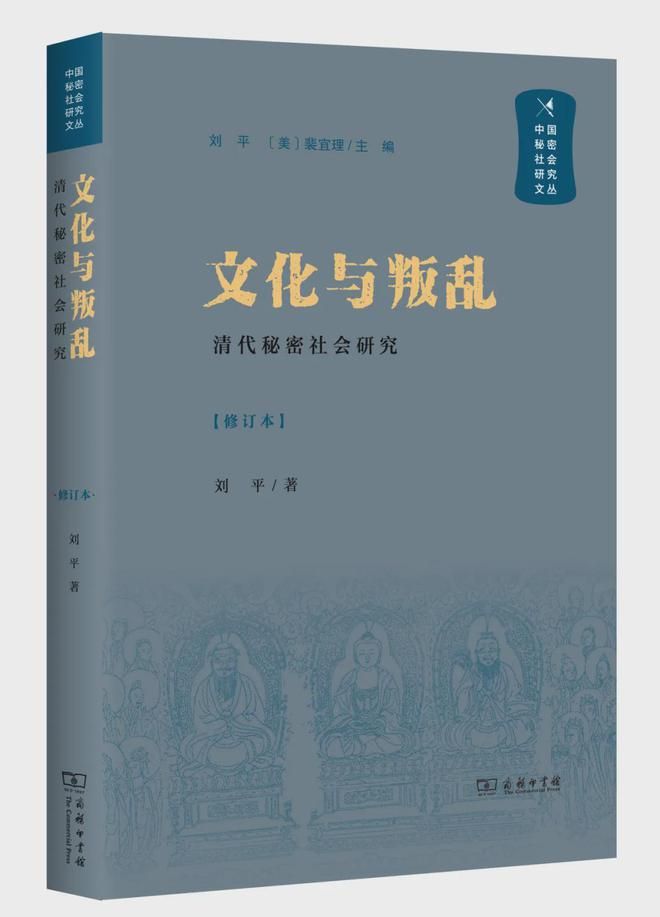
刘平 著
ISBN:978-7-100-23898-4
开本:16开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出版时间:2024年7月
定价:98.00元
内容简介
本书曾于2002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中国社会史主要开拓者之一、南京大学已故教授蔡少卿肯定该书的学术价值,认为“把中国秘密社会史研究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至今本书一直是秘密社会史研究领域非常重要的一部著述。此次为修订再版。该书从大众文化的角度审视清代秘密社会,从多方面揭示秘密社会存在的文化内涵和文化土壤,在此基础上对秘密社会的反叛行为进行剖析。全书的分析始于对文化传统的概念辨析。作者提出,“文化传统,意指文化传承,也就是以往社会流传下来的文化在当时与现时社会生活中的影响、流变”,“文化传统的两个显著特点便是人民性、延续性”,此概念是在强调被视作传统的文化,与近代、现代、当代并没有过多关系,不完全受到社会性质、社会制度的制约,是可以传承下去的,其中负面思想仍存有传播的空间。思考“文化如何被传承”这个问题及其深刻影响,是本书做出的最大贡献。
作者简介
刘平,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国秘密社会史、中国近现代社会史。现任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会副会长、上海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老子道学文化研究会常务理事等职。著有《被遗忘的战争——咸丰同治年间广东土客大械斗研究》(商务印书馆,2023年)、《中国秘密宗教史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等多种;译有《华南海盗(1790―1810)》、《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等多部。
本书目录
“造反有理”辨正(代序) 秦宝琦 / 1
导论 观察与思考 / 4
第一章 民间文化与民间信仰
——中国秘密社会存在的文化土壤 / 37
第一节 宗教、巫术、民俗等文化现象与历代农民
起义的关系 / 39
第二节 巫术的源流与演变 / 47
第三节 宗教的世俗化及宗教异端问题 / 60
第二章 清代秘密教门的文化内涵(一)
——对教门宝卷、叛乱思想的分析 / 92
第一节 宝卷与秘密教门的关系 / 92
第二节 叛乱根由——秘密教门的思想信仰简析 / 120
第三章 清代秘密教门的文化内涵(二)
——巫术、符咒、禁忌、气功等现象在教门中的反映 / 148
第一节 教门中的巫术、魔术、法术 / 149
第二节 教门中的符咒、谶谣、乩语 / 164
第三节 教门中的禁忌、戒律、隐语暗号 / 188
第四节 教门中的气功、按摩、武术 / 202
第四章 清代秘密会党的文化内涵 / 221
第一节 歃血盟誓、江湖义气对秘密会党的影响 / 222
第二节 秘密会党中的巫术、宗教因素 / 264
第三节 拜把结会、分类械斗与林爽文起义 / 296
结语 历史与现实之间 / 322
参考文献 / 336
后 记 / 348
修订本后记 / 350
导 论
(节 选)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社会史研究勃兴,对笔者的学术道路影响深远。当时,“史学危机”的阴影不断加深,社会史研究方法无疑给人们带来了一片亮丽,提供了一条可行的途径。从那以后,笔者便自觉与不自觉地与令人亦喜亦忧的社会史研究结缘了。
1988年,笔者进入南京大学历史系攻读硕士研究生,师从蔡少卿教授,研究近代会党与土匪问题。在宏观的研究视角和具体的研究方法上,蔡少卿老师的指导使笔者受益良多。从那以后,笔者一直在苦苦探索,其中最使我感到迷惘的是各学科之间的孤立性,例如中国农民战争问题,历史学家关心的是其过程;军事学家关心的是战略战术;宗教学家认为它是宗教研究的宠儿;文学家则一味高歌农民的反抗精神。而且,该领域的研究,尽管成果多多,但是,“多数研究基本上是诠释理论模式和说明公式化的规律”。这种条块分割的局面,根本不利于整个问题的深入研究,相反,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史学领域“五朵金花”之一的中国农民战争问题,在失去“政治”光环之后,迅速陷入了“门庭冷落车马稀”的尴尬境地。
实际上,近年来,许多学者都在呼吁加强各学科的合作,以带动本学科研究的深入。能不能换一个角度来研究历史问题,从而在某个领域里获得突破呢?1996年秋,笔者进入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攻读博士学位,师从中国秘密社会史研究专家秦宝琦教授。在与秦老师讨论选题时,秦老师征求笔者的意见。笔者提了三个题目,即“中国会党史”、“清代土匪问题”和“文化传统与清代社会叛乱”。前两个,是我比较熟悉的领域,后一个对我来说有一定难度。秦老师的答复很干脆,就选第三个。这样,一个机会,一次挑战出现了。
从那以后,笔者一直在围绕选题搜集材料、思考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笔者感到难度越来越大,压力越来越重。1998年6月,在博士论文开题报告会上,戴逸、秦宝琦、郭成康诸教授的意见使笔者“顿悟”出许多东西,尤其是戴逸教授提出了以下几点:
文化的分类,至少有上层文化和下层文化两种,要注意两者的相通之处与差异之处;
文化传统在下层社会中没有形成系统,但确实存在,核心之一是“义”及其相互关系;
文化娱乐在民间文化中十分重要,如“唱宝卷”,我就听过,很好听,是一种娱乐消遣,与儒家教育不一样,其内容荒诞、迷信,但在道德规范等方面,与儒家是相通的;
要注意文化传统是如何转变为“造反”的,不能忽视农民的经济苦难;
要区分农民起义和宗教起义;
民间的教门等组织,其思想信仰、组织、仪式等等,许多因素综合在一起,叛乱者利用了这种组织。
秦老师也特别强调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渊源及其涵盖面。他们的指点富有启迪。由此出发,笔者将文献资料的检索进一步扩大到了社会学、人类学、宗教学、民俗学、民间文学等领域。
1999年6月7日上午,在经历了紧张、充实的4个多小时后,笔者通过了题为《文化传统与社会叛乱——以清代秘密社会为视角》的博士论文答辩。答辩委员们的肯定性评语,笔者认真倾听;他们的批评性意见,我仔细做了笔录。笔者知道,凡事不辩不明,博士论文答辩这一环,乃是笔者的论文从幼稚走向成熟的基石。
1999年9月开始在南京大学做博士后的两年多时间里,我的任务之一就是这篇博士论文的修改、充实、提高。在联系出版社的过程中,几位资深编辑,如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的许医农先生、负责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东方历史文库”的阮芳纪先生、商务印书馆的王齐博士等人,从出版高质量学术著作的角度,向笔者提出了不少中肯的意见。他们的意见具有指导意义。
书稿成型后,最终确定题目为《文化与叛乱——以清代秘密社会为视角》,此次修订,定名为《文化与叛乱——清代秘密社会研究》。
本人博士学位论文题为《文化传统与社会叛乱》,现在的书名为《文化与叛乱——清代秘密社会研究》,两者之间有着内在联系。
所谓文化,《易·贲》云:“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中国人历来是将文化作为一个宽泛的“知识”概念来看待的。19世纪中期以后,世界现代化潮流奔涌,多种新学科崛起,人们研究文化的兴趣持续升温,进入20世纪,中国的政治家、哲学家、教育家也纷纷卷入给“文化”下定义的行列。至今,国内外关于“文化”的定义已有不下200种。
这里可举中国现代两位著名学者所作的定义,以观“文化”这个庞然大物之一斑。20世纪20年代,梁漱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称:“文化并非别的,乃是人类生活的样法。”二十多年后,梁漱溟又说,“文化,就是吾人生活所依靠之一切”,“文化之本义,应在经济、政治、乃至一切,无所不包”。梁启超认为:“文化者,人类心能所开释出来之有价值的共业也。”从他们的定义出发,我认为,文化概念大约可分为两种,一是广义的,一是狭义的。广义者,如梁漱溟所称,举凡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无所不包”;狭义者,应是人类的观念形态及其表现。后者与梁启超所言略同。这里,笔者无意与两位文化大师并列,也不想跻身于给“文化”下定义的行列,仅仅是想为本书的研究内容规定一定的范围——本书以“狭义的文化”为立足点。
什么是传统呢?《孟子·梁惠王下》云:“君子创业垂统,为可继也。”“继”与“传”通,唐陆德明《经典释文》云:“传者,相传继续也。”关于“统”,清段玉裁《说文解字经》云:“众丝皆得其首,是为‘统’。”“传”与“统”由单一概念转变为联词概念,是取“传”的相传继续和“统”的世代相承某种根本性的东西之意。张立文将“传统”的现代含义规定为:人类创造的不同形态的特质经由历史凝聚而沿传着、流变着的诸文化因素构成的有机系统。在现代汉语中,“传统”可作名词,也可作形容词,张立文显然是将其作为名词来加以解析的。
用作形容词的“传统”指的是过去的、消逝的意思,把它来与文化搭配,就是传统文化。在生活中、研究中,人们更常使用的是“传统文化”。那么,我为何要用“文化传统”呢?首先,据朱维铮称,历代相传的文化,大致可分为死文化和活文化。凡在历史上存在过、兴旺过,但在现代社会文化生活中已消逝的传统,如“玛雅文化、金字塔文化和中国的铜鼓文化、西夏文化等,属于死文化,相反,先辈们曾经认定是合宜的行为规范,以后继续被认为合宜,在现代生活中依然存在,尽管已经变了味并且变了形,那就是活文化”。
笔者认为,死文化、活文化的概念提得很好,至于前代流传下来的文化的“合宜”性,则不敢苟同,因为“人以群分”,此群认为合宜者,彼群未必认为合宜,如跨入民国后的张勋、袁世凯脑子里的皇权思想,从古及今中国社会中的迷信、溺女、械斗等现象,当然都是不合宜的。
其次,综合前述,本文的“文化传统”意指“文化传承”,也就是以往社会流传下来的文化在当时与现时社会生活中的影响、流变。
这里还要对“上层文化”“下层文化”和“大传统”“小传统”的问题作些分析。人类学家雷德菲尔德(Robert Redfield,1897—1958)在其1956年出版的《农民社会与文化》一书中,提出了“大传统”(Great Tradition)与“小传统”(Little Tradition)的概念。“大传统”是指“一个文明中,那些内省的少数人的传统”,“小传统”则是指“那些非内省的多数人的传统”;“大传统是在学校和教堂中培育出来的,小传统则是生长和存在于村落共同体文化中”。这里,雷氏显然是将“传统”与“文化”融为一体的。因此,其“大小传统”之分与以下一些概念如“高度文化和低度文化”“高雅文化与平俗文化”“神圣文化与世俗文化”等在意义上相近。
雷氏还认为,在有些文明中,这两种传统是很难区分清楚的。如在原始部落中,甚至可以讲没有大传统。而在两种传统可以区分的文明中,如中国和印度,大传统与小传统是互相影响的,主要表现在正统的哲学、宗教等精致文化向地方流动,逐步“地方化”(parochialization)。我在研究中发现,上层和下层文化也是互相影响的,有些下层文化后来逐渐上升为上层文化(如“道教文化”、如上古民间诗歌演变为《诗经》),有些上层文化也可变为“下层文化”(如“唐武宗灭佛”以后的佛教、摩尼教),更多的则是随着时间、环境的变化而互相消长。问题是,下层文化对于学界而言,还是一个少有接触或接触不深的领域。
“叛乱”一词,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国内史学界研究农民反抗问题时是基本不用甚至是持批判态度的。正如美国学者穆黛安(Dian Murray)所指出的: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中国学者对于大部分国内动乱一直都抱着一种僵化的观点。结果,那些说法夸大了民众运动的自觉性以及思想启示作用。
日本的历史学者往往用“反叛”、“叛乱”、“反乱”等词,意义相同。西方史学界,使用比较频繁的是rebellion,即造反、叛乱、反抗之意(国内一般译作“叛乱”),另一个相近的词是revolt(造反、起义、反叛之意),带有正义性的起义用uprising(起义、暴动之意),一般的反抗用protest(有抗议、反对之意,如“乡村民变”,在英文中便是rural protest),骚乱用disturbance、暴乱用disturbance或riot。我们在研究农民反抗问题时忌讳使用“叛乱”一词,并不在于“叛乱”的字面含义,而是在于特殊时代造成的政治含义。正如笔者在与人讨论博士论文题目的一次私人谈话中所受到的质问一样:“把农民起义视为‘叛乱’, 这不是站在封建政权的立场上讲话吗?”
但笔者仍然坚持己见,希望站在一个客观的立场来使用这个词。正如美国邪教问题专家玛格丽特·泰勒·辛格(Margaret T. Singh)所说:“不论某些邪教组织的行为如何招致外界成员的非议,‘邪教’一词本身不过是个描述性的词汇,并无贬义。”仔细思考一下,用“叛乱”是比较恰当的,它所评价的不仅是有远大抱负的农民领袖,还包括有私欲、有野心的首领;不仅指称正义性的农民起义,也包括纯宗教性起义、盗匪起事、民变、地方骚乱、暴乱等性质各异的动乱。无论正、反,都对封建统治秩序构成了威胁。
换言之,现在报章及法律指称当代新出的(包括外国的)异端教派(heterodox sects)或膜拜团体(cults)时都开始使用“邪教”一词,而“邪教”的正式出处是封建统治者,如嘉庆皇帝的《御制邪教说》即是,他是针对发动川楚大起义的白莲教说的,我们现在顺手“拿来”,大概没有站在嘉庆帝立场讲话的含义吧。所以,与“农民战争”“农民起义”“农民革命”这类词组比较而言,本书使用的“叛乱”是一个中性词。
从政治学角度来说,“叛乱”所包含的范围比较宽泛,如民族叛乱、宗教叛乱、统治阶级内部派别的叛乱(诸侯叛乱、宗藩叛乱)等。本书主要探讨的是以清代秘密社会为主要力量的农民为什么走上反抗道路的问题,以当时的社会状况及其变迁为考察依据,所指“叛乱”的主要内容有农民起义、秘密社会起事、盗匪起事、民变、民众骚乱(如械斗)等,故又曰“社会叛乱”,而行文中应用最多的可能是通俗的“起事”“起义”“造反”等词。
现在,本书名定为《文化与叛乱—清代秘密社会研究》,原因有二:一是为了简单明了起见;二是副标题已然勾勒出本课题的研究范围,“叛乱”之前没有必要再加“社会”一词。当然,在具体论述中,“文化传统”“社会叛乱”仍是常常要用到的。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本书主要以清代秘密社会为对象来探讨文化与叛乱的关系,剖析清代秘密社会生存、发展、反抗、演变的文化土壤,尤其是影响其思想信仰的文化因素,从而揭示农民反抗的深层原因。在此,有必要对“秘密社会”这一概念做些解释。
中国秘密社会史是历史学中一个十分艰深的领域,它以活跃在中国历史上的为数众多的秘密结社为研究对象。
一般来说,秘密结社是指那些具有秘密宗旨或教义、按照严格的秘密仪规从事地下活动的下层民间团体,由于各种秘密结社都是在秘密状态下进行活动,因而构成了一个外人不易了解、官方不易控制、正常社会秩序难以容忍的民众纠合体,人们通常称之为“秘密社会”。
秘密结社有以下三个特征:
1.非法性。由于它所奉行的秘密宗旨或教义对抗官方意识形态,其活动也不受官方约束,所以为法律所禁止,只能非法存在。
2.神秘性。秘密结社都有自己的入会入教仪式、联络方法和赏罚规章,这使它具有极大的凝聚力和保密性,其特异的隐语、标志、口号及其传授方式等,很难为人识破。另外,秘密结社所选择的崇拜偶像,来自宗教、神话乃至传说中的英雄豪杰,加上施符上表、吃斋诵经或开山立堂、结盟拜会等似教非教的方式,令人神秘莫测。
3.反社会性。秘密结社的基本信众大多为破产农民、城市平民、手工业者、商贩、运夫、船民、水手乃至僧道医卜、散兵游勇,一方面他们抱成一团,相依为命,具有互助意义;另一方面,这类人良莠混杂,不少人桀骜不驯,常有很大的盲目性和破坏性。
秘密结社的异端思想和非法活动,尤其是经常反抗政府的起义,对王朝秩序构成很大威胁。历代政府莫不从法律上加以禁止,从军事上加以镇压。此外,秘密结社成员为生计所迫,除了进行正当的经济斗争外,又往往呼朋引类、劫掠窝赃、欺行霸市,直至杀人越货。因此,秘密结社的活动对正常的社会秩序有很大的破坏作用。对于他们的活动,我们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千万要避免或捧上天、或掼诸地的做法。
清朝是一个秘密结社空前繁多的朝代。根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档案的记载,清政府统计出当时的秘密结社名目有215种,其中清政府立案侦查以至于留下档案可查的就有111种。有人估计清代秘密结社总数不会少于三四百种。
对清代秘密结社的分类,一向有“南会北教”之说。“会”是指会党,以天地会为主体,活跃于福建、台湾、两广和长江流域一些省份。小刀会、三点会、三合会、哥老会、仁义会、江湖会等名目是它的支派。“教”是指教门,流行于中国北方各省,例如白莲教、天理教、八卦教、义和拳、一贯道、大刀会、红枪会,等等。这种划分很粗糙,且不说清中叶以前教门之独领风骚,即使是在清季至民国,南方之教门,北方之帮会,都是有着极大势力的。尽管如此,我们可从这一角度窥见清代秘密结社分布的大致情形。